From the Collection of George Walden (Lots 2501-2544)
華爾頓藏中國書畫(編號2501-2544)

George Walden
本輯源自英國外交官華爾頓 (George Walden,b.1939) 。畢業於劍橋大學,後赴莫斯科大學深造。一九六二年入英國外交部,自始開啟逾廿載之外交生涯。六五年被派往香港大學學習中文,後任駐北京代辦處二等秘書。七○年後歷任駐法國大使館一等秘書、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書等。離任後參選國會,在八三至九七年間連續三屆任保守黨國會議員。他勤於筆耕,多年來在報章撰寫專欄,出版著作十餘種。

George Walden and lot 2539 Zhang Daqian's Lady hung behind him
華爾頓於六七至七〇年間於役北京,適值「文革」熾熱期間,因嗜中國藝術,遂視文物商店如狂熱環境中之平靜綠洲,不時造訪,尤於琉璃廠北京市文物商店收穫最豐。所藏以晚清以降名家書畫作品為主,無拘名氣,純以個人興趣及品味作入藏準則,尤以二十世紀京華名家之作數量近半,如姚華家藏陳師曾書畫數件、溥儒近四尺整幅〈雪山行旅〉、于非闇晚年力作〈雪竹山鷓〉,兼及齊白石、王夢白、湯定之等作,各具特色,堪爲故都藝壇風貌大觀。此外,如黃賓虹、吳昌碩書畫數幅,金石氣息濃厚,頗異於西方審美觀,可窺其獨特眼光。上文錄於華爾頓自傳,憶述當年往文物商店購買書畫之經歷、與店員間之交往,文字詼諧生動,側寫當年社會環境,亦反映對中國文化之理解。
輯中各件多保持六十年代或以前裝裱,多具文物商店貨品標簽及當年購買發票。部份曾參加六八年十二月於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舉辦之小型展覽,與英、法、瑞典等國駐華外交人員藏品一並展出,僅供使館人員及外國駐華新聞工作者參觀。華爾頓歸國後,藏品未有示人,至今已逾半世紀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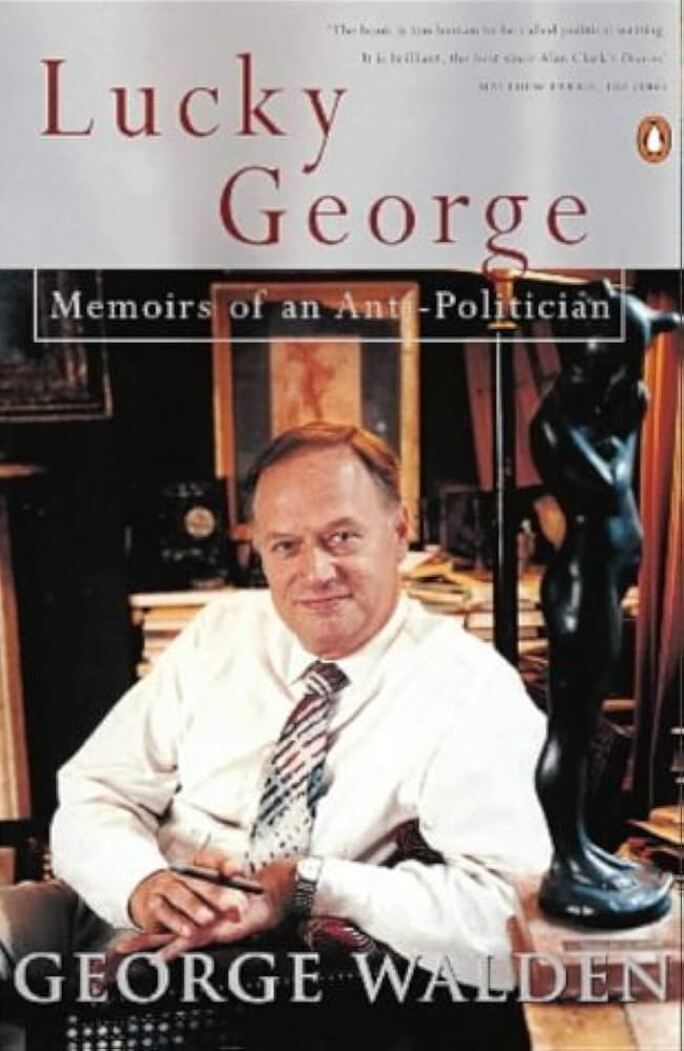
Cover of Lucky George: Memoirs of an Anti-politician, written by George Walden
一九六六至六九年間,我主要以外交人員的身份待在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,我想從當時喧鬧的社會環境中喘一口氣,便天天跑去字畫店,那是一方難得的平靜綠洲。字畫店位於城中心週邊的曲折小道, 昔日是北平的文物買賣中心,今已大半凋空:不僅中國沒遊客,連本地人也沒法在此做生意。
字畫店員一副僧人模樣,腳履拖遝,目光低垂,沉著寡言。神色如履薄冰,他們是「舊」物專家,經手的買賣難以歸類。他們總站在店的院子,我呼喚完他們,便在店裡候著,等他們注意到我。店內掛滿字畫︰宛如筆走龍蛇法書的紫藤、臨流倚坐的高士、逸筆草草或工筆細寫的山水,與街道上的死氣沉沉天淵之別,教人精神一振。店裡除了我,鮮有其他客人。但凡我出現,店員便拖著細碎的步伐從院子走進店裡,像年長而敏捷的蟹。表面看來,他們穿著寬垮藍色衣服與牛仔布凱皮帽,可是待人接物的柔和手段,以及鑒畫精准的眼光,足以揭示他們真實的身份:他們是披著工人服的美學能手。
他們起初顯得冷漠怯懾,小心翼翼地掩飾舊式文化的禮數。不說「您好」,笑容欠奉,只粗魯咕噥應對,和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一樣。互動最初並不順暢。我知道心儀畫家的名字,可要是直接問他們是否有畫家的作品,能否看一下,於我並無好處。這種單刀直入的處事方式,並不奏效,對方只會抿起嘴巴,眉頭緊蹙。
以前,店員會按部就班,先奉茶,寒暄一下,籠統聊聊書畫,然後談某幾幅畫,接下來,如果你表現興趣,就集中談一幀畫。最後,一番討價還價後,促成買賣。現在,他只是站在那。在國營店鋪,員工根本沒意銷售,這是某種反商業行為,跡近安東尼奧尼〈春光乍泄〉電影中不願賣東西的漫畫店長。情況膠著,這實際有違書畫店員的本能。他們懂畫,也尊重畫,恨不得讓我買最好最貴的畫。
於是,經過一次次拜訪,一層層推進,我們終於建立起默契來。首先,我會親切堅定地跟店員打招呼,他會嘀咕以應。當外國客人恰如其分地被怠慢後,便可進入正題了。我不會直接說想買哪畫家,反之,我會對牆上的畫表達興趣。我心知那都是次等的,但萬事總要起頭。頭一個月,店員仍然諸多顧忌,不主動讓我看更多畫。然後,憑著無比熱誠,以及刨根問底的態度,不停問他這個畫家影響力如何,那個畫家又如何,我把店員引導到他最喜歡的領域:書畫專業。
他們進入教學狀態,開始指導我。當我指向牆上的畫,他們會說,不錯,是個有意思的小名頭畫家,不過這畫不怎麼好。你看,這線條,或是這用色。早歲的中等作品,不是晚年最好那類。即便是最好的畫,他的用色仍略嫌太猛,構圖太彆扭。你想想,真正的大師會如何發揮那片荷葉啊!店員會拋出一些響噹噹的名字,比如黃賓虹或吳昌碩,一邊搖頭,好像萬分惋惜的樣子。
這才算大師啊!這幾筆下得多妙,那幾筆掃得多大膽!那可是花九十載才練就的本領。這位(店員指向牆)是他學生。模仿得有形無神的,畫時才六十歲。六十歲的人,能指望什麼?可惜的是,大師的畫總是難以遇上,遇上時,偏偏又價格不菲。
店員按捺不住了,恢復那套舊式的銷售說詞。此刻,他已認清我是認真的買家。但他愈看清這點,愈會滔滔不絕的延長前戲,非要我想離開才休止。
「等一會!」到了此刻,老人終於叫我停下腳步。他仿佛剛憶起什麼的似的,在立軸下面的櫃子翻找。這櫃我一進門就注意到了,也知道該把希望寄託於此。他躬著身,在立軸堆中煞有介事地翻來覆去,抽出一軸。接著,一言不發地用長杆把畫掛在牆頭,緩慢地,賞心悅目地,讓畫幅在手上舒展開來。
中國畫最引人入勝的部分,莫過於把畫展開的瞬間。開畫這舉動,就在樹梢第一朵花蕾展露之際,或是山巔雲靄示人一刻,也能讓中國人,尤其是沉溺鑒賞之人,炫耀他們的專業知識。開畫的絕竅是,要趕在有足夠線索曝光之前,把畫家名說出來,不然就引不起對方讚歎了。
可是老人依然忍口不說,他盯著我的目光,在展開傑作時,一邊悄悄期待我的反應,一邊流露得意的神情。當我大贊「真厲害!」,他會滿意地哼鼻子咕噥回應。 「看看這兒——還有這兒!是不是—?」我遲疑地問,就算我肯定畫家是誰,也得讓老人滿足告訴我的欲望。
「不不不!」他竊笑,儘管我什麼名字也沒說出口。 「壓根兒不是他!那是——」然後他會吐出一個名字。 「他是滬上的,老是這樣畫梅花。」
如果下一步要還價的話,我會收斂一下,不表現得那麼雀躍。可是他知道,我也知道,他根本不在乎價錢。討價還價是不可能的。他會裝模作樣地吊顧客的胃口,把好戲留到最後,放長線給大魚,然後一把釣起來,平靜地享受勝利一刻。
我樂於當那條魚,可是一談到價錢,就沒戲唱了。他可以演活一場舊式買賣,可演不了還價的戲碼。這步驟由國家掌控。價格都寫在標籤上。你要麼買下它,要麼別買。而就算是仿作,或者是「擬⋯⋯法寫成」的,也會標示出來,定價會相應的訂便宜些。他們不會嘗試說服你以假當真。反商業本質的店也有其好處。
這些我都知道,他當然也知道,可是這戲還沒演完。我是真心對價格好奇。當我驚歎完了,再三嘴嚼過畫面之美後,會試探問道:「這算貴吧?」
「是的,相對上算貴」,他會滿意的嘴角上揚,邊伸手接我付的款,收下對他來說頗為可觀的銀碼,享受當書畫買手快感的餘韻。 「比較」——是常掛在口邊的詞。大部分的中國事物都可相對「比較」。你或許會問:「跟什麼比較呢?」,答案大概是五千年的歷史吧。
某程度上,書畫價格是他們的煩惱,多於是我的煩惱。我的工資無處可花,二級秘書工資有多少,我就能買多少。另一邊廂,對中國人而言,由於經濟無法獨立,又對外封閉,他們無法參考市場制定價錢。在一個無買賣或賺錢動機的國家,給不認可的畫定價,去賣給不認可的客人,肯定讓人頭疼。
但凡參與此事的人,可能是老人他們,都面對兩難局面。要是價格訂太高,可能會被指控將陳腐的文化舊物價值估計過高。要是訂太低了,同樣會面臨將國有財產以過低價格賣給外國人的指控。老人肯定把這些想透了。價格,相對來說,都訂得中規中矩。
有時我會好奇,他們如何看待外國人買中國畫這事。這些畫算不上是中國內最珍貴的文物,可畢竟是近代文化的一部份,是十九到二十世紀最一流的書畫作品。當我終於離開中國時,我窺見了中國人對此事的態度,只是沒想到,對方是跟我年紀相若的年輕夥子。
海關人員要求外交人員于出境時把行李清關, 我帶著沉重的心情把六十幀卷軸交上去。海關人員令我打開。我選了一件小東西,慢慢展開︰「這是吳湖帆的」,我說,「他是個上海畫家。」
年青的海關人員一臉不悅。我拿著打開的卷軸,站著不動,擔心最害怕的事要發生。
「下一件!」
我展開另一幀畫,這幅精細的花卉才剛冒出上方幾吋,我還沒來得及說畫家是誰,年青人就大喊︰「吳昌碩。下一件!」
我察覺到他眼鏡後露出一絲得意神情。我展開第三幀。只瞥一眼山巒頂就足夠了。
「黃賓虹!下一件!」
如是者,他看遍了所有卷軸,辨識出每個畫家,就這樣批了出口文件,放行所有作品。
他雖然年青,對書畫卻明顯見識不凡。翻閱書畫時,他識出的畫家一字不差。專攻書畫的人,肯定也是愛畫之人。看著我把這些畫帶走,就算不說出口,他也肯定很心痛。要是有一天,事情都平息了,我或許會回來,跟他好好討論中國書畫。
十五年後,我真的回到中國了,那是與卡靈頓勳爵同行的外訪,當時我擔任他私人秘書。在華兩天,有次公務完了,我馬上就想到去畫軸店,就問大使館的人店是否還營業。他們說店家搬家,去了城中新的文物商區。
我到訪了新店,逗留了一陣子。店裡客人更多了,畫軸的量少了,品質較次,價格卻更高了。店裡的老人已不在,新的店員年輕,態度客氣,處變不驚。我問一位年輕的女店員,生意好嗎?
「生意好啊,還挺忙的」,她回道,轉身招呼一位美國旅客去了。
── 摘自華爾頓〈幸運的喬治〉